常常,在谈论中国电影的未来时,很多人习惯开口就抱怨广电总局设置的条条框框。在他们“遗憾”的语气里,好像没有这些条框华语电影就能一飞冲天,好像没有这些七七八八的约束我们的电影人就能凭空拍出好几百部《教父》或是好几千部《东京物语》来。
是的,没人可以否认华语电影正处在前所未见的畸形年代。绝大多数观众包括我在内,仍将华人之光李安当做最后一根稻草,即便他老人家在《卧虎藏龙》之后就再没拍过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华语电影了。可事实上,好电影并没有绝迹。而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当一部真正的好电影克服一切险阻、披荆斩棘浑身是血的闯到我们面前时,我们又是否能去辨别,能去相信,能去给予一部优秀作品应得的褒奖呢?而不仅仅是在若干年后,以资深影迷的口吻向身边人介绍“你们知道吗?当年这部不被看好的作品其实是部佳作。”
我们总是以蓦然回首的姿态来对待这些作品,似乎它们生来就是深埋地下的瑰宝,不需要镁光灯的注目,不需要掌声尖叫,只需要老老实实的躺在土堆里,坐等阡陌骚客迎门。
对于一部优秀的电影而言,这显然不公平。
在《八月》上映的两周前,我就在课上不礼貌的预测这部电影注定将步《钢的琴》或是《心迷宫》的后尘。纵使张大磊,张猛,忻钰坤们已经用各自最大的善意与诚意来对待这个恶意时代的电影市场。只是奈何,把这三部作品的演员列表加在一块,能被广大观众叫得出名字的也仅仅只有王千源、秦海璐。至于什么霍卫民、邵胜杰,什么张晨、郭燕芸们则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再看剧本,三部电影无一例外的将视野锁定到小镇,小村,描绘庸碌细碎中衍生而出的梦想,生杀,罪恶,亲情。这其中,《钢的琴》与《八月》尤为类似,在刻意做旧的复古镜头下,斑驳的老城吃力地呼吸着,慢悠悠地丈量着。废弃的炼钢厂、倾倒的老烟囱、不合时宜的DISCO、失业的母亲与父辈们的兄弟情、电影将尘封在相片里的年华染上了稍纵即逝的质地,显得迷人而脆弱。
只是这份对旧时光的感动也仅仅到此为止了,现在的观众再也耐不下性子看穷人和普通人的故事。无论戏里戏外,我们对精英文化的崇拜正在次元式增长。托尼斯塔克、布鲁斯韦恩,他们如此风靡的原因不仅仅因为他们伸张正义,而更在于他们拥有与其科技相匹配的强大财富。就像现在的小孩总是不喜欢让衣着普通的父母来接自己放学,你要说他们不爱父母吧?其实并不是。只是这样的亲情在孩子们眼里是一件平庸的事情,而酷和个性恰恰是他们一切行为的准则。
一群空有演技却没名气的演员,扭扭捏捏讲一堆下里巴人的鸡毛蒜皮。是啊,再没什么东西比这种电影更令人厌倦的了。我们的观众早已深陷音响效果和IMAX的殿堂中,电影镜头越来越短,爆破声却越来越大、明星的片酬越来越离谱,可就连最基本的笑容都让人尴尬得出戏。特殊效果,明星效应抢了剧本和表演的风头、甚至完全取代了后者的地位。所以当《八月》还未上映时,我就明白已经有无数口口声声自称影迷的人们在心里枪毙了它。而结果不出所有人意料,这部描绘中国九十年代初西部小城的“卑微”影像没能战胜有史以来最魁梧、最会打飞机的金刚。至于走出影院足够成为谈资的,似乎也只有高过树林的大蜘蛛、不太刷牙的暴食蜥蜴、还有历经磨难九死一生却依然端庄白皙的景甜。
事实上,我并不认为金刚的压倒性胜利有什么不对。这只与怪兽之王哥斯拉相爱相杀的大猩猩配得上如此殊荣,用尖端特效打造的骷髅岛也的确符合我们对人间炼狱的定义。只是相对的,我同情《八月》是因为他的死来得太快也太轻易了。而更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还会再一次醒悟,再一次回过头为他点赞,再一次向朋友推荐这部冷门的,不被人关注的作品。只是这些关注永远只会发生在过去时。
我有时候在想,若是让小津安二郎再活一次,在此时此刻的中国公映他的《浮草》或是《东京物语》会是怎样。“平庸的主题!无非就是嫁女儿嘛!我在电影院坐两个小时就为了看一家人吵了又好,好了又吵?”是的,小津也满足不了我们。
在中国,真正的好电影永远只有一种死法。而由明星小鲜肉摆拍而成的PPT却能轻轻松松赚他个百八十亿。也许中国电影百病缠身,千错万错,错在体制,错在剧本,错在态度,错在静与动的抉择。只是身为观众的我们逃无可逃的,也是这出错误的组成部分,因为我们本可以救下一些作品,可最终还是选择祭奠它们的墓碑。
by——熊猫妈妈
2017.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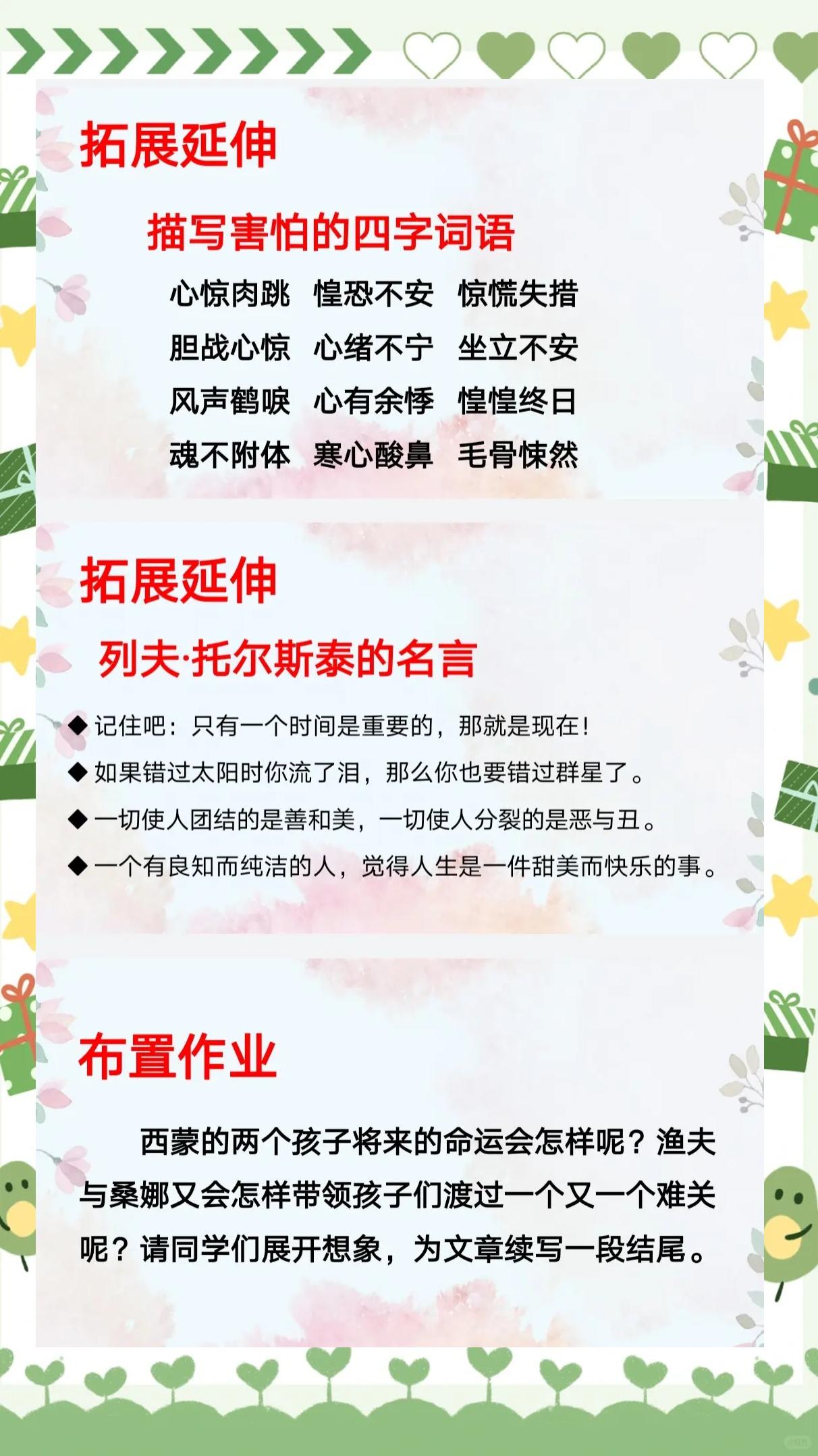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00000000001号
京公网安备11000000000001号 京ICP备11000001号
京ICP备11000001号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